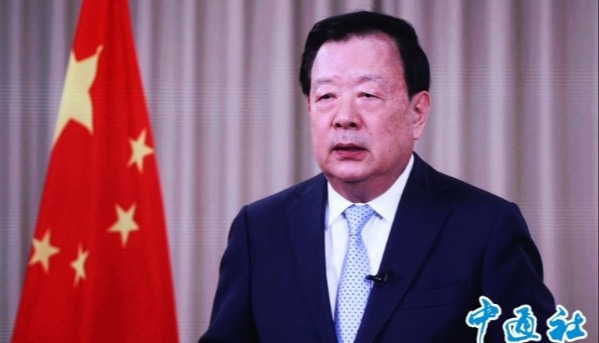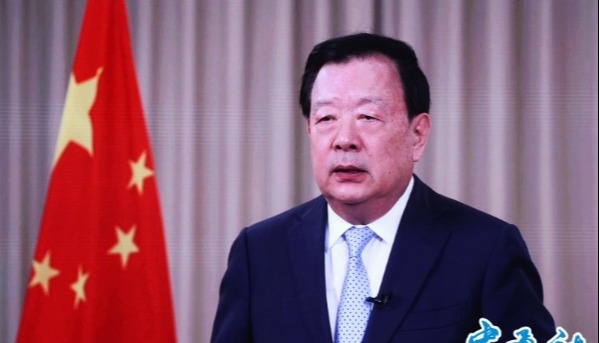名家點評《紅樓夢》人物(2)陳寅恪認為,最偉大、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,所謂“情之最上者,世無其人。懸空設想,而甘為之死,如《牡丹亭》之杜麗娘是也。”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,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。《牡丹亭》就是這樣一本千古絕唱的劇本。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,即便不能結合,也為其忠貞不渝,矢誌不變。如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。《紅樓夢》也正是這樣一部癡人說夢式的理想主義小說。第三個層次,則是“曾一度枕席,而永久紀念不忘,如司棋與潘又安。”這又是《紅樓夢》中的稍具現實主義色彩的例子了。第四個層次,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的,普通民眾通常都可接受的愛情與婚姻模式,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。這樣的婚姻生活以平淡為基調,以穩定為最高準則,為愛而生、為愛而死的戲劇性與故事性縮減至最低值。至於第五個層次,則純粹是貪圖欲望。 在陳寅恪的擇偶觀中,重心是在學術上的登峰造極,而絕非為了一己之情愛。他的擇偶觀是落在戲劇、小說與文藝作品之外的現實抉擇,作為一生以追求卓越學術成就的大學問家,他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追尋愛情的理想國。 1926年,35歲的陳寅恪結束了國外求學生涯,歸國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,與王國維、梁啟超、趙元任一起並稱“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”。由於長期以來潛心學業、心無旁騖,加之陳寅恪認為自己體弱多病,恐累及他人,故一直未婚。這時,其母親俞氏已逝世,父親陳三立一再催促其速速成婚,但陳寅恪始終未承允。在親友及學院同仁的多番催促與大力撮合之下,到了1928年,歷經三年“催婚”的國學導師,方才與唐篔在上海結婚。這一年陳寅恪38歲,唐篔30歲。 從此,他們攜手白頭,至死不渝。其間歷盡劫波、同舟共濟,自不必贅言,其情感與婚姻,足可稱學界典範,亦毋庸置疑。那麽,使後世讀者頗感興趣的,無非是這樣的結合,如果按照陳氏的擇偶觀來看,又屬於第幾個層次呢? 誠然,可以為一代名妓柳如是作別傳的陳寅恪,從學術理想上看,似乎向往的是前兩個層次的“佳偶”。但這兩個層次都不屬於正常的世俗婚姻,也不可能為一介書生提供一個穩定安逸的家庭生活。退而求其次,第三個、第四個層次的擇偶觀,才符合常態下的世俗婚姻。陳寅恪的身份是現實中的學者,而非戲劇、小說中的俠客與癡情公子,他的婚姻只能定格於安穩的世俗婚姻而已。與同是“海歸”精英的胡適相比,陳並無包辦婚姻之催迫,並沒有一歸國即完婚的約束,原本是有自由戀愛的空間與時間的。奈何親友“催婚”之下,歸國三年即成婚;與唐篔的結合也是經同仁介紹,認識之後不久即完婚,並無什麽戀戀風塵的浪漫歷程。曾經做過許廣平老師的唐篔,就此成為陳的賢內助,甘於為夫君的學術生涯默默奉獻。
紫鵑(清)改琦 繪
初擬“妙玉”頗自喜,終了最愛是“紫鵑” 提到陳寅恪,免不了就會想到吳宓。二人本即摯友,早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,陳、吳二人與湯用彤便被譽為“哈佛三傑”。歸國後,吳宓乃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,而陳氏則被聘入國學院任導師。二人可謂伯牙子期,高山流水遇知音。 據說,陳、吳二人的交誼,還是因一首關於《紅樓夢》的詩而致“友情益摯”的。早在1919年,也就是陳與吳談起“五等愛情論”之際,吳恰又在哈佛演講《紅樓夢新談》,陳為之作詩題詞,足見陳、吳二人確因《紅樓夢》互引知音、締為摯友。事實上,吳宓不但個人極愛讀《紅樓夢》,學術上也曾著力研究《紅樓夢》,還將研究心得作為授課內容,在大學課堂上多次講述。稍稍翻檢上個世紀的一些舊報刊,不難發現,這位曾經以西洋文學研究及國學傳承為己任的吳教授,一度以“紅學家”身份,頻頻亮相於課堂與報道之中。 譬如1949年11月24日的重慶《大公晚報》之上,就刊發有一條題為《紅學專家講紅樓夢》的簡訊,報道稱,“吳宓教授將應南泉新專學生請,赴該校講‘紅樓夢研究’”。那麽,當時吳宓怎麽會滯留在西南後方,怎麽還在重慶任教授課呢?抗戰期間,吳宓先是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,後來又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,抗戰勝利後,他為何沒有隨校遷返北平,為何還要在西南一隅講授他的“紅樓夢研究”呢? 原來,抗戰勝利之際,吳宓即有意擇居後方,決意遠離中心城市,以期靜心專註於學術研究,不再受世事紛擾。1945年9月,吳宓到四川大學外文系任教授,1946年2月,又推辭了浙江大學、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,到湖北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,1947年1月起主編《武漢日報·文學副刊》一年。其間,清華大學梅貽琦一再邀其返歸北平任教,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其摯友陳寅恪為號召,力邀其出任該校文學院院長……面對這些紛馳南北的盛邀,吳宓一律未允,竟於1949年4月底飛赴重慶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,還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,算是正式入蜀定居了。 正是在入蜀定居之初,吳宓開始重拾其多年研讀《紅樓夢》的心得,開始樂於講授並研討《紅樓夢》相關專題了。時間回溯到1949年5月24日,《大公晚報》上就刊有一組總題為《遠鄉同學紛作歸計,吳宓教授講紅樓夢》的簡訊,專門報道重慶相輝學院內的師生動向。 試想,在國民黨政權行將崩潰的情形之下,“陪都”重慶各大院校人心浮動,相輝學校已然有二百余學生離校,剛入校任教不久的吳宓,卻一改平時“很少活動”的生活狀況,應邀去做主題為“紅樓夢”的講演了。這樣的做派,如果不是極愛《紅樓夢》者,恐怕是很難做到的。 事實上,還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,吳宓便已顯露出濃厚的“紅學”興趣,圈子內外都漸以“紅學家”視之。1947年3月6日,吳宓更將其《紅樓夢》讀書心得全盤托出,撰成一篇長稿,公開發表在了武漢《力行日報》之上。此舉倒不是為了給學生們授業解惑,也不是為了與別的“紅學家”切磋研討,最初的起因,只是為了澄清朋友圈裏一度稱其為“妙玉”化身的戲談。此文開篇首段,明確表達了為文初衷,吳宓這樣寫道: 昔年在清華園中聚餐,同座諸友以《石頭記》中人物互擬。劉文典教授以宓擬妙玉,謂宓“氣質美如蘭,才華馨比仙”,我實愧不敢當。然心中亦頗自喜。南渡後,居昆明,乃改《世難容》曲,以自悼自況。於是世傳宓嘗妙玉雲雲,其實非也……然宓於《石頭記》中人物,所最愛敬而“雖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者,厥為紫鵑。 原來,吳宓在清華任教時,曾與諸多友朋以《紅樓夢》中的小說人物相互比擬。這就類似於近現代文化圈裏曾流行一時的什麽“文壇點將錄”、“畫壇點將錄”之類,是將文學文藝領域內的一些傑出或活躍人物,用《水滸傳》一百零八將的名目來加以比擬。而吳宓一幫人,則是用《紅樓夢》人物來加以比擬的,自然又別有風趣。 清華友朋之中,著名學者劉文典將吳宓比擬為“妙玉”。吳宓雖“愧不敢當”,“然心中亦頗自喜”。這相當於說,吳宓當時是表面上謙稱不可,而內心卻對這樣的比擬感到“自喜”的。“七七事變”爆發之後,吳宓隨清華師生南遷至雲南昆明,一度仍以妙玉的精神氣質“自悼自況”。不過,情隨世變,時過境遷,在流徒西南後方的後半生歷程中,吳宓終於發現,原來自己最愛是“紫鵑”。 於是,吳宓寫成了這一篇《論紫鵑》,在武漢的報紙《力行日報》上全文發表了出來。此舉一方面要說明自己從精神氣質與情懷寄托上而言,已不是先前友人們評說的那樣接近於“妙玉”了;另一方面,則是要表達自己確實非常推崇“紫鵑”的情懷與操守,如果可能的話,自己的後半生更願意盡力做一位像“紫鵑”那樣的人物。 之所以那麽推崇“紫鵑”,吳宓的理由非常充分:簡言之,這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。認定“紫鵑”是一位忠於理想的人,乃是出於其傾心愛護、全力守護“林黛玉”之故。吳宓為之解釋稱: 《石頭記》一書所寫之理想精神,為“美”與“愛情”,而此理想與此精神完全表現寄托於林黛玉之一身。林黛玉者,美與愛情之結晶也。黛玉既為此理想與精神之代表,不得不終生憂傷憔悴痛苦呻吟,而彼時大觀園中能同情而贊助林黛玉者誰乎?曰:紫鵑一人而已。 一番解釋之後,吳宓遂列舉《紅樓夢》回目中關涉紫鵑的多處情節,逐一點評其“忠於理想,甘為理想犧牲”的種種事跡,可謂贊佩之至。文末,吳宓向親友世人宣稱: 詩雲: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,吾實敬愛其人。吾願效絜紫鵑,且願引紫鵑以自勉,終吾之余年也。吾親吾友,欲知宓者,請睹紫鵑! 這一文末宣言,足見這年過半百的吳大教授,的確已將“紫鵑”視作了自己的靈魂楷模,確實是愛“紫鵑”愛得深沈啊! 聯系到吳宓晚年的景況,那“忠於理想”的甘苦自知,那近於“紫鵑”的生涯行跡,既可謂一語成讖,亦可謂求仁得仁。當然,這樣的比擬與說辭,幾乎又回到“索隱派”的做派,那是“舊紅學”的老套,可不是“新紅學”的旨趣。在此,權作題外話而已。 |